目录
快速导航-

首读 | 一盏蜂蜜
首读 | 一盏蜂蜜
-
首读 | 所到之处,无不卑微
首读 | 所到之处,无不卑微
-
首读 | 苦的甜
首读 | 苦的甜
-

短篇小说 | 大雨将至
短篇小说 | 大雨将至
-
短篇小说 | 赵小敏的梦想
短篇小说 | 赵小敏的梦想
-

中篇小说 | 白猫
中篇小说 | 白猫
-

纸贵 | 住院记
纸贵 | 住院记
-
纸贵 | 人间清影
纸贵 | 人间清影
-
纸贵 | 奇妙之旅
纸贵 | 奇妙之旅
-
纸贵 | 卜居洛阳城
纸贵 | 卜居洛阳城
-
纸贵 | 父亲
纸贵 | 父亲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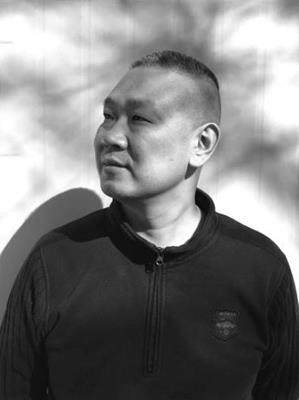
咏絮 | 李昌鹏的诗
咏絮 | 李昌鹏的诗
-
咏絮 | 龙门(外四首)
咏絮 | 龙门(外四首)
-
咏絮 | 未名海(组诗)
咏絮 | 未名海(组诗)
-
咏絮 | 短诗集束
咏絮 | 短诗集束
-
洛阳故事·新安篇 | 桃花盛开
洛阳故事·新安篇 | 桃花盛开
-
洛阳故事·新安篇 | 五月樱桃红
洛阳故事·新安篇 | 五月樱桃红
-
洛阳故事·新安篇 | 雨润青要山
洛阳故事·新安篇 | 雨润青要山
-

新蕾 | 桂花雨
新蕾 | 桂花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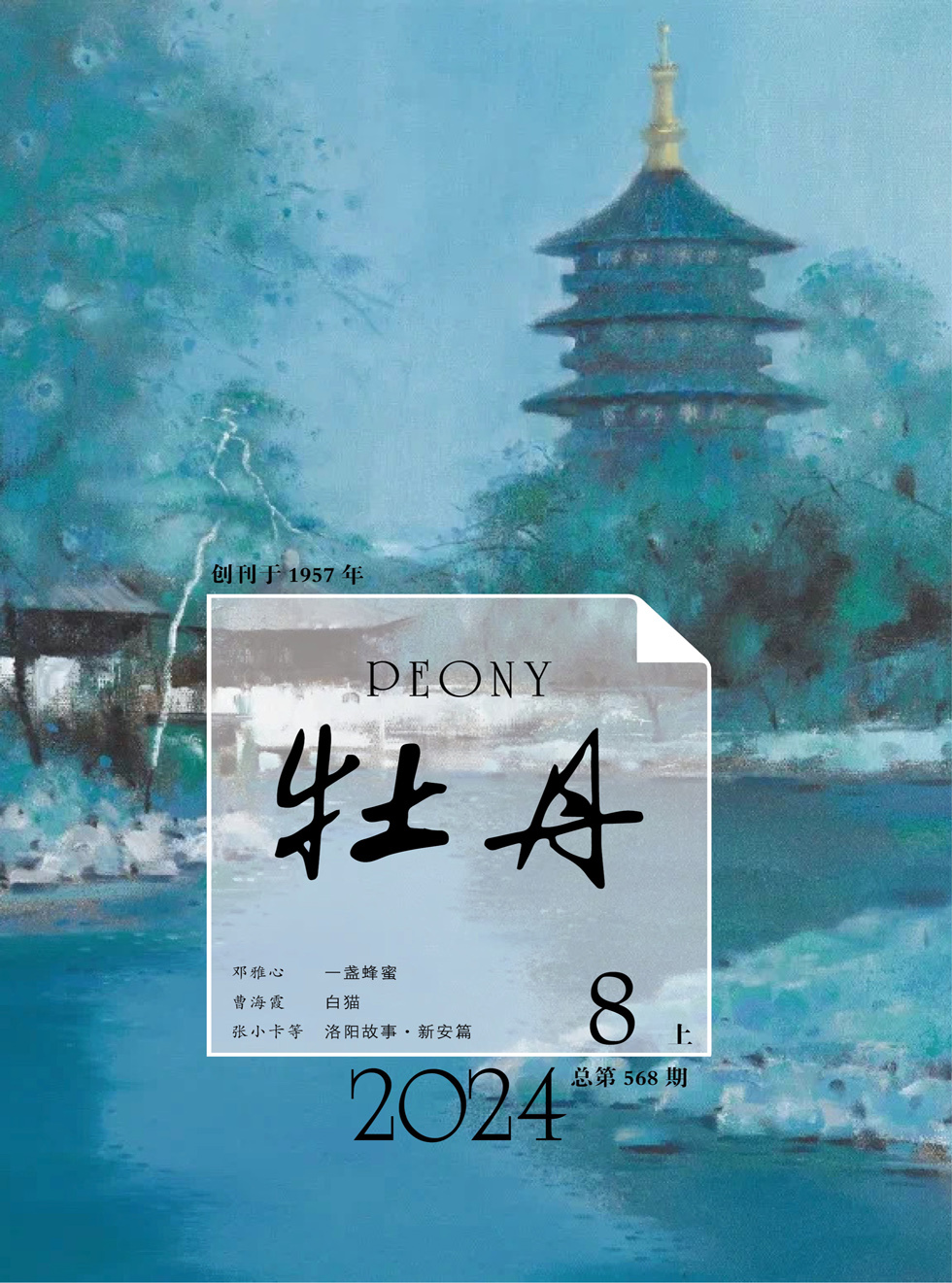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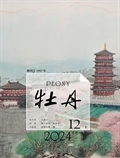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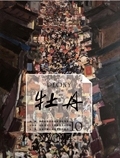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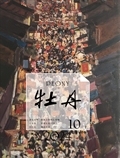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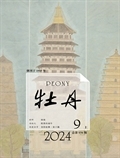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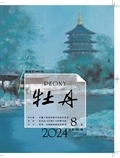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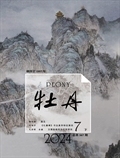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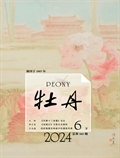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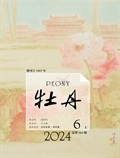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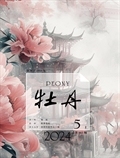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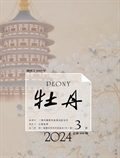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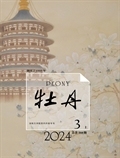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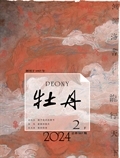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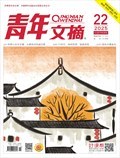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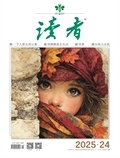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