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亲人依旧 | 淑慧
亲人依旧 | 淑慧
-
亲人依旧 | 慈乌夜啼
亲人依旧 | 慈乌夜啼
-
亲人依旧 | 你在,爸妈不老
亲人依旧 | 你在,爸妈不老
-
亲人依旧 | 陪父亲戒烟的那段日子
亲人依旧 | 陪父亲戒烟的那段日子
-
亲人依旧 | 母亲大人的亲笔信
亲人依旧 | 母亲大人的亲笔信
-
亲人依旧 | 为失忆母亲打造“儿童乐园”
亲人依旧 | 为失忆母亲打造“儿童乐园”
-
亲人依旧 | 两颗尘土也要相亲相爱
亲人依旧 | 两颗尘土也要相亲相爱
-
情路漫漫 | 父母的罗曼蒂克
情路漫漫 | 父母的罗曼蒂克
-
情路漫漫 | 真正的爱都在细节里
情路漫漫 | 真正的爱都在细节里
-
情路漫漫 | 和外科医生恋爱的日常
情路漫漫 | 和外科医生恋爱的日常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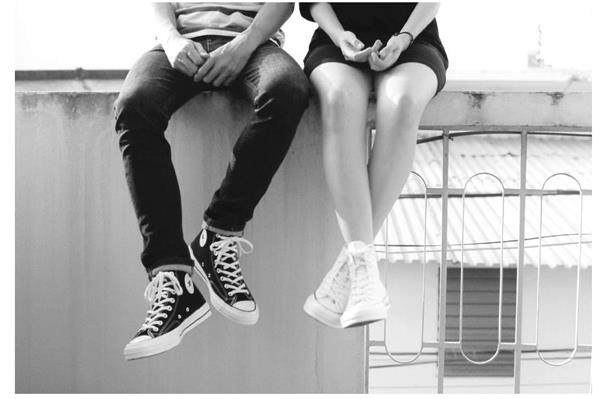
情路漫漫 | 这份爱情潜伏了很多年
情路漫漫 | 这份爱情潜伏了很多年
-
情路漫漫 | 还是输给了那场爱情长跑
情路漫漫 | 还是输给了那场爱情长跑
-
围城内外 | 花些心思相亲相爱
围城内外 | 花些心思相亲相爱
-

围城内外 | 妻子创业,我愿做她背后的男人
围城内外 | 妻子创业,我愿做她背后的男人
-
围城内外 | 爱情的模样是好好相处
围城内外 | 爱情的模样是好好相处
-

围城内外 | 傅首尔:幸福人设,是这辈子最大的意外
围城内外 | 傅首尔:幸福人设,是这辈子最大的意外
-
围城内外 | 冷静,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方方面面
围城内外 | 冷静,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方方面面
-
励志小品 | 人生的“三把钥匙”
励志小品 | 人生的“三把钥匙”
-
励志小品 | 独处是生命的良田
励志小品 | 独处是生命的良田
-
励志小品 | 余生,别忘取悦自己
励志小品 | 余生,别忘取悦自己
-

励志小品 | 无论多远,请找到我
励志小品 | 无论多远,请找到我
-
励志小品 | 真正见过世面的人,大多不动声色
励志小品 | 真正见过世面的人,大多不动声色
-

家庭保健 | “精致穷”? 搞不好就是“穷讲究”
家庭保健 | “精致穷”? 搞不好就是“穷讲究”
-
家庭保健 | 学会和情绪对话
家庭保健 | 学会和情绪对话
-
家庭保健 | 家庭和谐与教育方式,对孩子青春期心理的影响
家庭保健 | 家庭和谐与教育方式,对孩子青春期心理的影响
-
成长印记 | 同学们,用心理剧来调节情绪
成长印记 | 同学们,用心理剧来调节情绪
-
成长印记 | 懂,比爱更重要
成长印记 | 懂,比爱更重要
-

成长印记 | 别动不动给孩子贴标签
成长印记 | 别动不动给孩子贴标签
-

成长印记 | 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:背后的故事好有爱
成长印记 | 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:背后的故事好有爱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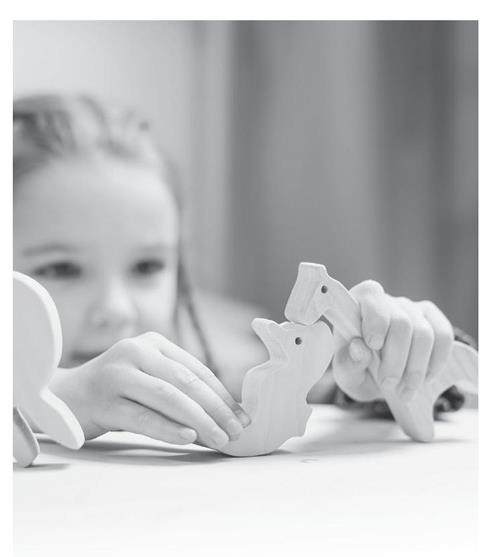
成长印记 | 童言童语,需要要引导
成长印记 | 童言童语,需要要引导
-
成长印记 | 小班幼儿该怎么上厕所
成长印记 | 小班幼儿该怎么上厕所
-
成长印记 | 小学生识字,怎样教才有用有趣
成长印记 | 小学生识字,怎样教才有用有趣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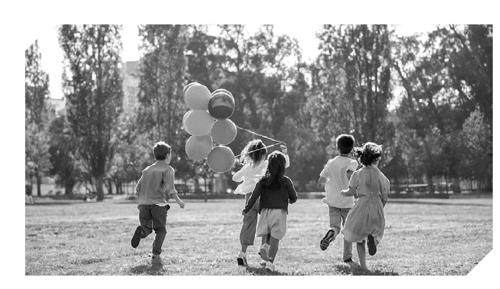
成长印记 | 如何培养一个心理阳光的孩子
成长印记 | 如何培养一个心理阳光的孩子
-
教育论坛 | 乡村美育教育的创新
教育论坛 | 乡村美育教育的创新
-

教育论坛 | 小朋友快来乐享“布之趣”
教育论坛 | 小朋友快来乐享“布之趣”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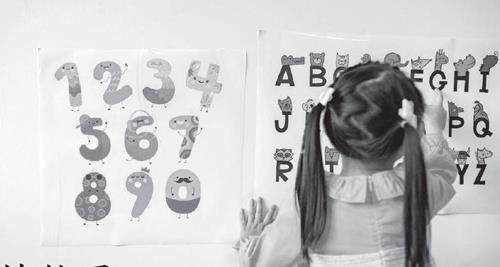
教育论坛 | “听说读写”:低年级数学课堂的妙用
教育论坛 | “听说读写”:低年级数学课堂的妙用
-
教育论坛 | 问题情境:如何在儿童木工活动中深度学习
教育论坛 | 问题情境:如何在儿童木工活动中深度学习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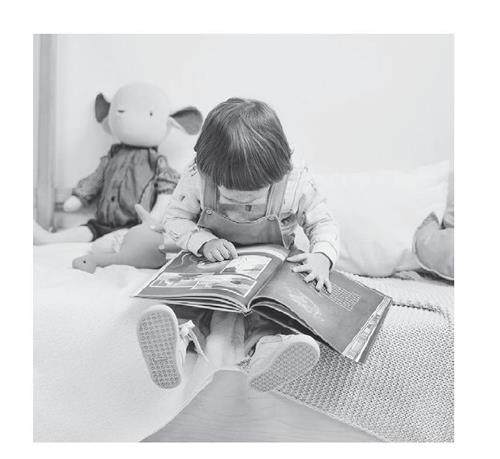
教育论坛 | 巧借绘本,给幼儿搭艺术“立交桥”
教育论坛 | 巧借绘本,给幼儿搭艺术“立交桥”
-
教育论坛 | 别出界,孩子你在玩“区域游戏”
教育论坛 | 别出界,孩子你在玩“区域游戏”
-

人在旅途 | “家委会”到底要做什么
人在旅途 | “家委会”到底要做什么
-

人在旅途 | 岫岩满族剪纸的“文化基因”
人在旅途 | 岫岩满族剪纸的“文化基因”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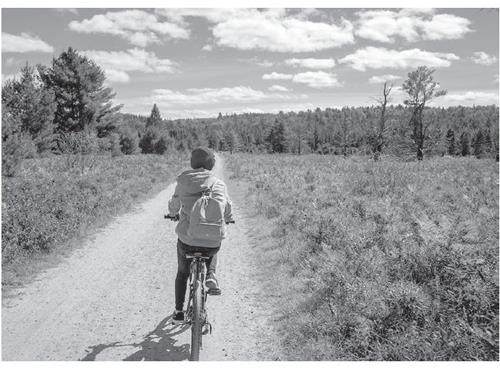
人在旅途 | 村妇联如何参与村庄事务管理
人在旅途 | 村妇联如何参与村庄事务管理
-
人在旅途 | 大学生创业:一个心理公众号的诞生和成长
人在旅途 | 大学生创业:一个心理公众号的诞生和成长
-
开心一刻 | 我的妈妈有点Man
开心一刻 | 我的妈妈有点Man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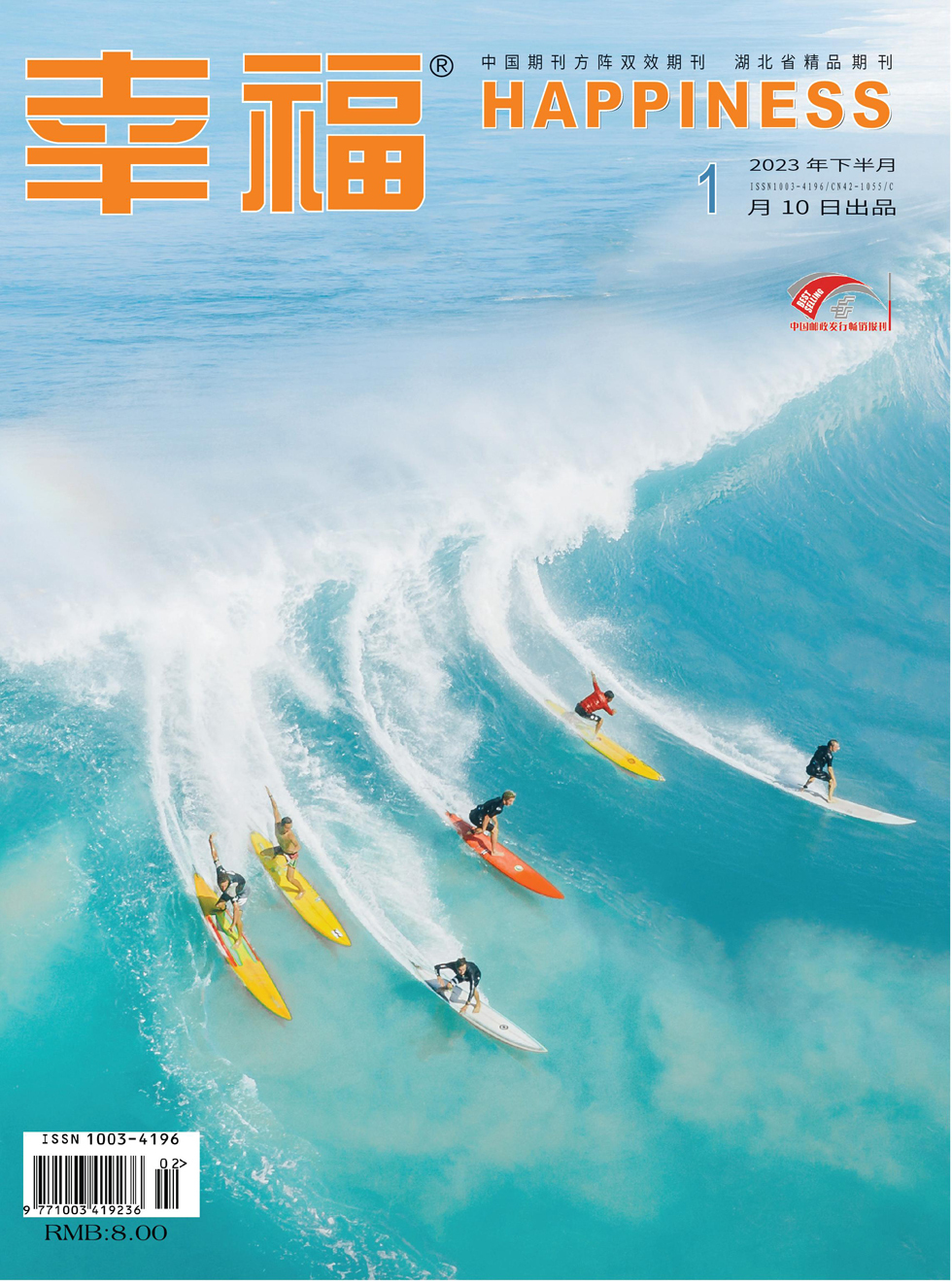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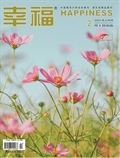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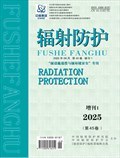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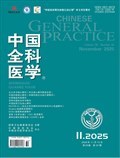





 登录
登录